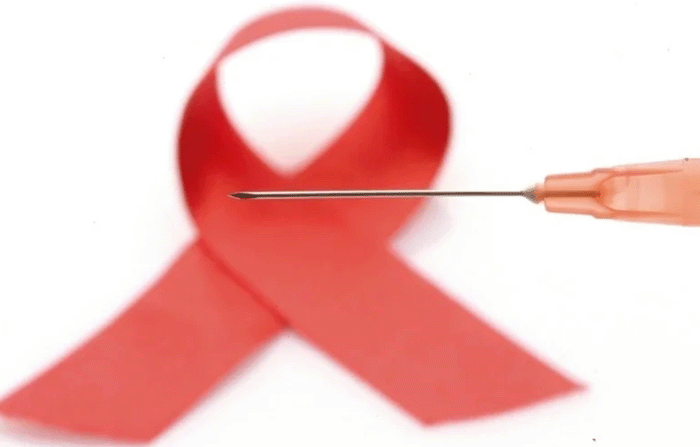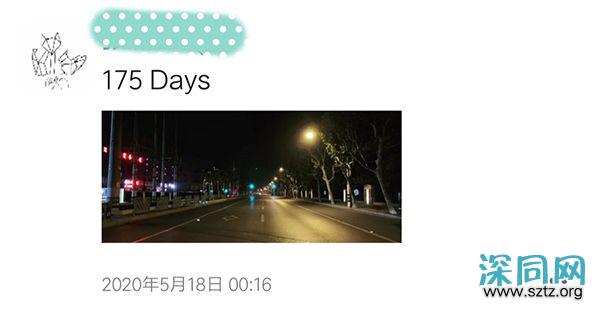40年同性恋球迷专访:我是同性恋,我应该在这里
时间:2017-10-09 08:53出处:资讯阅读:129 编辑:@www.sztz77.com
《footballpink》的这篇采访深度描述了一个关于“傲慢与偏见”的故事。我们可想象,当一名同性恋者坐在球场上,而周围人全部在齐声高喊侮辱同性恋的歌曲或口号,在四万名观众中感到无助的孤独,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达瑞尔-特列斯最终找到了一群和他一样特殊的人,在这个组织中他得到了安慰,但要求平等、与那些偏见的斗争将无时无刻不在继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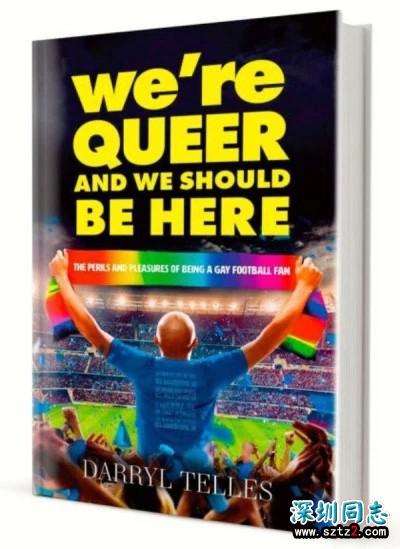
(图)图为达瑞尔-特列斯著作的封面
达瑞尔-特列斯(Darryl Telles)是《我们是同性恋,我们应该在这里:作为一个同性恋球迷的危险和快乐》(《We’re Queer and We Should Be Here: The perils and pleasures of being a gay football fan》)一书的作者。这本书里讲述了自1970年以来,他本人作为一名同性恋热刺球迷的诸多回忆。特列斯是“托特纳姆骄傲的白百合”最早的成员之一,这是一个同性恋热刺球迷组织。
在他的回忆录中,特列斯带着读者一起回忆了托特纳姆热刺在英格兰和欧洲客场征战时的一些故事,他在看台上遇见恐同症的经历,以及同性恋球迷群体是如何改变了他作为一个人或粉丝的生活等等。在这次采访中,我们将讨论足球领域的同性恋话题以及同性恋人群的现状。
这是从一个光头开始的
乔希:你哥哥是切尔西球迷,为什么你是热刺球迷?
达瑞尔:好吧,就像书中说的那样,我们遇到了两个光头,一个是热刺球迷,一个是切尔西球迷。他们问我们支持哪支球队,所以哥哥选择了切尔西,我选择了热刺,我真的是被迫选择的。还有,我是来自芬奇利(属于大伦敦巴尼特市),所以要么是热刺,要么就是切尔西。我选择了(芬奇利)右边的俱乐部,这只能是热刺,也是距离(我家)最近的英超俱乐部。
第一次球场受辱
乔希:你现场观看热刺的第一场比赛是怎么样的?
达瑞尔:直到1978年我才去观看比赛,那时我大约14岁,那次正好是在我14岁生日过后。
在那些日子里,足球场内外发生了许多球迷骚乱事件。如果我去观看热刺比赛的话,我母亲认为这会非常不安全。所以,我就和一个朋友一起,从学校直接出发了。那是令人惊奇的体验,在露天看台上,你和所有的人一起在拥挤的人群中推推挤挤,到处都是兴奋的人群。另外,托特纳姆热刺那时刚刚从次级联赛中升级上来,我们刚刚在乙级联赛呆了一年。我们也刚刚从赢得了世界杯的阿根廷签下了阿迪尼斯和维拉。所以,我感觉非常兴奋,还有一点儿害怕和恐惧。我能很清楚地记得这件事情……
我们的对手是诺丁汉森林,就像人们所熟知的,诺丁汉森林刚刚赢得了联赛冠军,所以这是一场非常重大的比赛。因为和助理教练彼得-泰勒的友谊,人们嘲弄他们的主帅布莱恩-克劳夫是一个同性恋。在看台上,这样的歌声传了过来。所以从我看球的第一场比赛算起,这样性质的歌声就从来没有间断过。那时候人们也会有一些像“faggot”或者“酷儿(queer)”(注:这些词汇均对同性恋者高度冒犯)这样类型的评论。这些都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人们几乎一直在说的,根本没有人会认真考虑这件事。
乔希:那时候你已经出柜了吗?或者你在那个时候知道自己是同性恋吗?
达瑞尔:是的,我想我知道我是同性恋,实际上从我8岁或7岁起(我就知道),所以这是很早的。我还没有出柜,但我想我知道这不是我要经历的一个阶段或者任何事情。是的,当我观看比赛的时候,我会说我是同性恋,但我还没有遇到别的人,所以我没有任何性经验,但是我知道我是同性恋。
加入GSFN
乔希:你在什么时候决定成为同性恋足球支持者网络最早的成员之一?这是怎么发生的?
达瑞尔:当我在1986年从大学回来的时候,我真的不能去足球场了。其中一个原因是我没有朋友一起去看热刺比赛,我和我在学校的朋友们没有联系,我也很少有机会独自去玩,我觉得自己很孤立,一个同性恋球迷太容易受到伤害了。所以,我去看了一两场比赛,但不经常去。直到1989年,我在《同志日报(Gay Times)》上看到了一则广告,里面提到了要建立一个同性恋足球支持者网络,我对此做出了回应。大概是在1989年的秋天,我去参加了我第一次的会议。
乔希:你提到了你曾在那些比赛中感到很容易受到伤害,很孤独。在你最终加入GFSN(同性恋足球支持者网络)后,情况有什么不同吗?您能否将前后情况比较、对比一下?

(图)“托特纳姆骄傲的白百合”组织的官方网站
达瑞尔:这就像……这真的,就像天堂一样。我一直认为我可能只是少数几个热爱足球、支持足球的男同性恋者之一。当我来到GFSN时,我发现更多的人都和我一样深爱着足球,我在想“天啊,这太棒了”,而那些朋友们现在仍然是我非常亲密的朋友。这是一个真正的剧变,一个真正改变我生活的变化,因为足球对我太重要了。虽说1989年(我就加入了GFSN),到了1991年我才买到了季票。当我回头来看,(来到GFSN)这很重要。过去独自看球时,当你听到某些评论时你只能保持安静,否则人们就会对你说那些特别带有性别歧视的言论,你几乎不得不去遵从它或者就去忘掉它。现在和团体在一起时,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尤其是在主场比赛的时候,你知道这是相当公开的。
乔希:那什么会伤害你更多?是那些评论,还是喊叫或者歌声?
达瑞尔: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是那些评论。因为你会和你周围的人说话,然后突然他们就会说这些话。此外,作为亚裔,很多种族主义仍然在这里盛行。事实上,我想说的是,70年代的环境要严酷和恐怖得多。上世纪80年代末,当我读完大学回来看球的时候,黑人球员已经多了很多,所以歧视行为稍稍平息了一些,但仍会有些种族主义色彩的言论。
乔希:在你加入GFSN之前,当你在比赛中感到孤独的时候,支撑你超越、忍受这些的力量来自于哪里?
达瑞尔:我必须诚实,我没有超越或者足以忍受。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再去观看比赛的原因。每个赛季我只会去一到两场比赛,对于那些真正喜欢足球的人来说,这确实有点儿伤感。所以我不得不在电视上看看球,我也有一些异性朋友,当我和她们一起去看比赛的时候,她们很能理解我是同性恋的事实。但后来GFSN出现了,这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
“自相残杀”
乔希:你在书中提到过最引人注目的一个故事,是2011年你在布莱顿的时候,当时布莱顿和托特纳姆热刺有一场赛季前的友谊赛。你能给听众介绍一下那个故事吗?
达瑞尔:我在那年3月搬到了布赖顿,因为我的工作地点已经换到了伦敦桥(注:到布莱顿距离很近),而我在布莱顿有朋友。这样做是有意义的。对于一个独自生活的中年男人来说,伦敦已经变得非常孤独,既不友好,而且也相当昂贵。尤其重要的一点,布莱顿似乎对同性恋者更加友好,气氛更加和睦,所以我搬到了那里。那是布莱顿在刚刚建成的美国运通社区球场举行的首场比赛,是场友谊赛。坐在那偌大的球场中,我感到非常心烦意乱,周围有憎恶同性恋的诵唱在响起。 我不会认为这是托特纳姆球迷们无恶意的玩笑,我甚至不能以一种温柔和幽默的方式提到这件事。我就在那里,我是一名独自呆在那里的同性恋者,再一次我要面对自己这一方的球迷唱着喊着这些东西。我再一次感到非常愤怒,我不能挑战它或者也不能对这种情形做点什么。我想在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思考,回顾过去这些年发生的一切,也许有些事情并没有改变。也许我需要写一本书了,那是我开始考虑写这本书的时候。
乔希:在他们吟唱的那一刻,你说你什么都不能做。有没有可能与球场安保部门对话,或者你认为他们不会听这个?
达瑞尔:这是一个很好的观点,但我没有那样做。我只是坐在那里,愤怒而不参与。我想问题是在那些日子里,当一群人都在喊着唱着时,除了自己坐下来或者让人们坐下来,管理人员能做的真的十分有限。我想看到一个公共广播系统,人们可以在里公共系统里解决这类问题……当这些言辞来自于个人的时候你会更容易接受,我不得不说,当面对一群人时我感受不到足够的自信。即便是现在已经过去了30年,当时在看台上那种无助的感觉仍然会袭来。除非有人和我在一起,否则我会觉得很困难。
乔希:是的,那一定很可怕。
达瑞尔:嗯,我想是的,尤其你要面对自己主队球迷们的时候……
乔希:那年晚些时候,布莱顿实际上也来到了托特纳姆(的主场)。
达瑞尔:是的,实际上是几个赛季之后。我认为是2013年,甚至是2014年。我们在联赛杯的比赛中与布莱顿对阵,当时“骄傲的白百合”已经建立起来了。所以,这是对我们角色的一个很好的测试。因为这是我们的领地,这是我们家白鹿巷,我们不想重复发生在那里的事情。

(图)“托特纳姆桥骄傲的白百合”组织的彩虹旗出现在球场
乔希:谢谢你提起来这件事,因为我也想加入“托特纳姆白百合”这个托特纳姆同性恋支持者组织。对于那些不知道白百合角色的人来说呢?
达瑞尔:嗯,大概在2011-2012赛季(注:可能达瑞尔记错了,当时索尔-坎贝尔是自由球员),在面对后来去了阿森纳的索尔-坎贝尔(热刺青训出身)时,热刺球迷的诵唱非常富有攻击性,带有强烈的种族色彩而且也表现出了对同性恋的憎恶。我对其中一些诵唱的的感觉实在是太强烈了。为了荣誉,热刺管理部门,热刺董事会和整个俱乐部都对此持反对的态度。俱乐部宣称,任何一个喊着恐同言论的人都将被禁止入场观赛。他们还联系了GFSN,成立了一个球迷团体支持者俱乐部,为同性恋者提供相关的支持。这是对于我们这个群体真正的认可,显示出了一种包容的态度。当然,这和我们组织的扩展有一定关系。在80年代,我们组织的主要群体是男同性恋者,现在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人也都加入了进来。这是一种官方的认可,刹那间就让你感觉像是夏天来到了一样。你要知道,我们得到了官方的支持、认可和帮助。电视节目中有一些关于我们的东西,网站上也有一些东西。最重要的是,在比赛当中有一面巨大的彩虹旗,我相信你们的听众已经看到了,因为它已经通过电视传遍了世界。
足球社区反应
乔希:你在书中提到,你有机会遇到很多人,很多球员还有很多裁判。就白百合以及其他许多同性恋支持者团体或网络所做的工作而言,他们会有什么反应?
达瑞尔:无论如何,我仍然认为,在和恐同症的作战当中,我们需要提高的还有很多。你会发现让球员们谈论种族主义、反种族主义和女性足球是很容易的事,但我认为顶级足球运动员在反对同性恋恐惧症的问题上仍然存在问题。我很高兴看到保罗-博格巴最近说,如果一个同性恋球员出柜了,他不会对此有任何看法。如果能看到更多这样的情况,特别是从国际球员那里,这将是件好事。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我认为有时候他们会害怕与这个问题牵扯在一起。我无法理解这些,但这似乎就是恐惧。因此,我希望看到更多的来自球员本身的支持,支持这场足球场上的反恐同运动。我仍然认为,谈论种族主义和女性足球是一种轻微的倾向,人们并没有真正谈论到能够影响LGBT球迷的问题。
乔希:你认为球队、英足总或国际足联最好能做些什么?因为很明显,他们可以和球员们做很多事情。
达瑞尔:是的,这些当局者,我很难过,我在书中说过。以英足总为例,他们的领导总是那些会忽略同性恋球员的人,他们害怕来自于球迷们的敌意,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无论从原则上说,还是从事实上来说,我都认为这是一种错误。我真的认为在看台上已经发生了变化,如果球员们出柜了,事情并没有想象的糟糕。因此,有时候我认为作为当局者,尤其是英足总,在这个问题上真的看起来十分昏聩和恐惧,而他们真的不应该这样。我认为他们需要掌握主动权,真正支持这场活动。不仅仅是当一个球员出柜或可能出柜时这样,他们应该连续不断地支持这场运动。在我的书中,我谈到过关于性平等教育的一件事。当人们讲出不当言辞或类似的东西时,他们应该被送去上平等教育的课程。如果你想要推行这场运动,我认为每位教练,每位主帅,每位董事长都需要从一开始就有这种平等意识。所以我希望看到每个人都能参与到这个培训项目中,而不仅仅是那些言辞冒犯的人。如果我们给出了这种明确的信号,更多的年轻男女同性恋球员就会选择在青训期出柜,然后在他们的职业生涯中,他们会成为同性恋、双性恋或者变性人。

(图)前英格兰女足队员埃尼-阿卢科曾公开指责教练种族歧视
乔希:我们都看到了埃尼-阿卢科(Eni Aluko)的情况,我的意思是这明显与种族主义不同,但她谈到了平等教育实在是太有必要了,所有的教练也都需要一些平等的教育。
达瑞尔:绝对是的。我认为这是一个问题,我觉得英足总是认为它的球迷们会做出过激反应。
是的,可能会有反应,但是你要去解决这个问题。我认为,在板凳席和更衣室里,人们仍然在接受一种大男子主义、恃强凌弱和辱骂的文化。我认为这是很有“说服力”的,我认为它能“说服”很多同性恋者不要出柜。这才是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我越来越多地谈到了足球运动员,你刚到提到阿卢科的例子也是。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是足球内部的文化,而不是看台上的文化,这需要改变。
谁将是第一个?
乔希:你提到足球运动员有点儿需要出柜。但主教练和训练员们又如何呢?我知道伯恩茅斯的摄影师是非常公开的,她是一位变性人。教练、球探们该怎么做?
达瑞尔:哦,是的,大家的原则要始终如一。我们之前谈论过一名裁判,他是第一个出柜的职业裁判。所以,是的,它必须贯穿整个足球。在考虑了所有的情况后我们必须记住,球场和足球是很多人的工作场所和职业,就像其他任何工作场所或职业一样,同性恋者不得不隐瞒自己的取向是不可接受的。所以,足球真的需要迎头赶上。

(图)伯恩茅斯的摄影师非常勇敢
乔希:就像教练或者球员,需要多长时间才会有人出柜呢?
达瑞尔:我想可能是在我们的青训营里,年轻的球员们(会做到),希望我们能在不久的将来可以看到这一点。我认为,一旦一个或两个人出柜被人们普遍接受了,就像黑人球员的形象和女性裁判等问题一样,我认为就可能会有一个反弹的开始。我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无论人们的性取向会是什么,都将不会是一种障碍,人们会更加关注球员是否优秀,教练是否公正和受人尊重。
我们正在失去同性恋球员
乔希:如果你是足球运动员或者教练,你会出柜吗?
达瑞尔:我想我必须要这样做。在我的生活中,在我的工作中,在我的家庭里,在我的员工、雇主和我的朋友们面前之时,我都在面对这个问题。那是我生命中出现的一种倾向,我不能想象对所有人都不公开。我无法想象这会给我带来什么样的压力,我想可能会有很多同性恋球员会因为压力退出比赛。在比我们想象的更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失去了这些同性恋足球运动员。我必须要出柜,但我没有优秀到能够去踢足球。